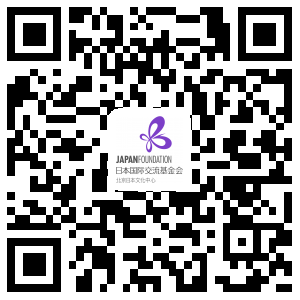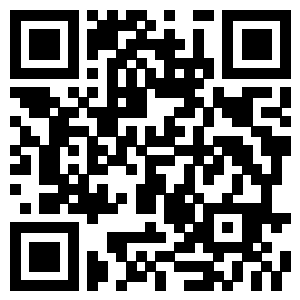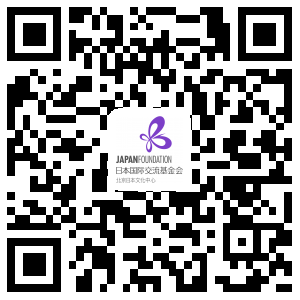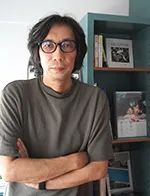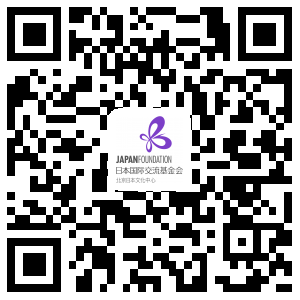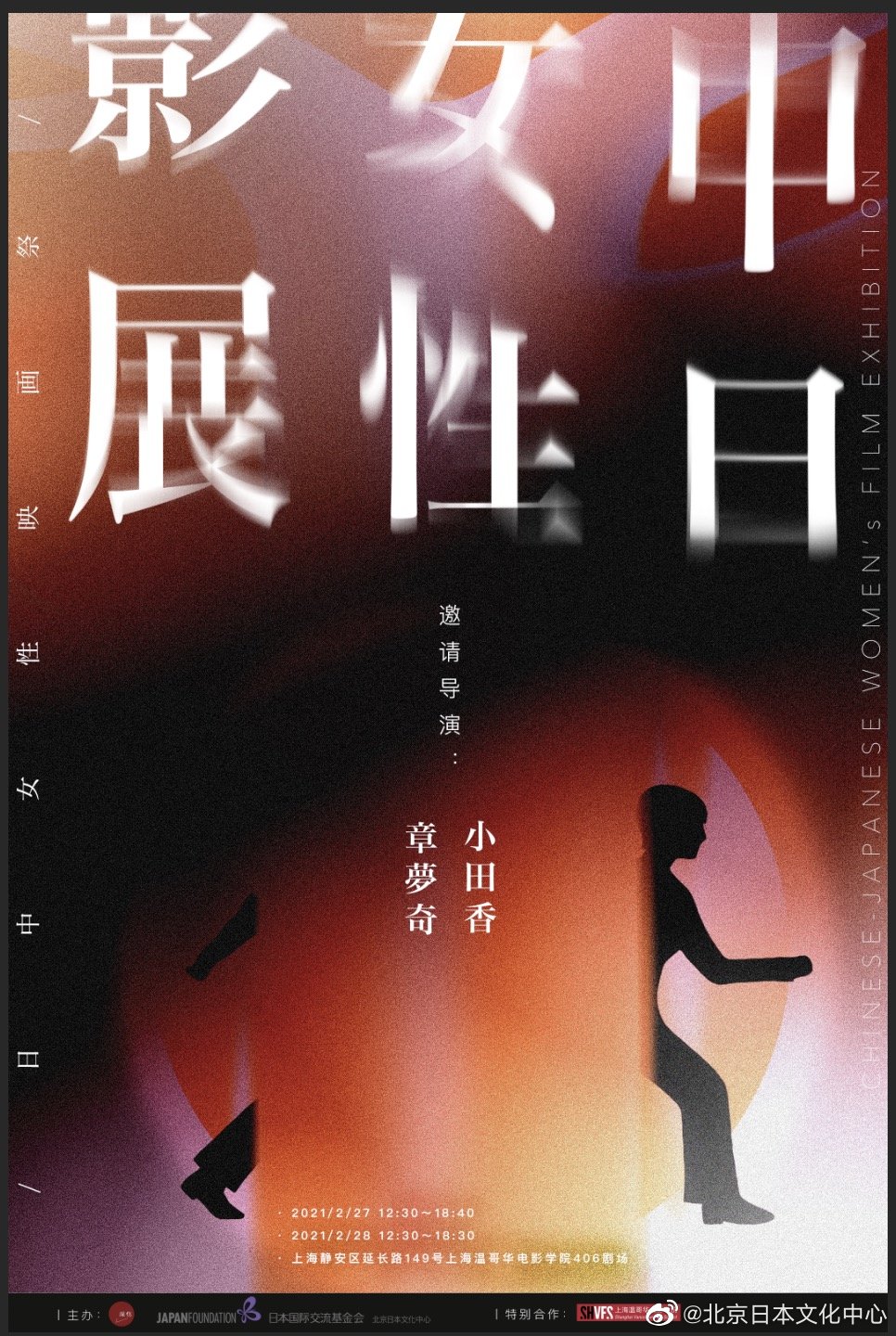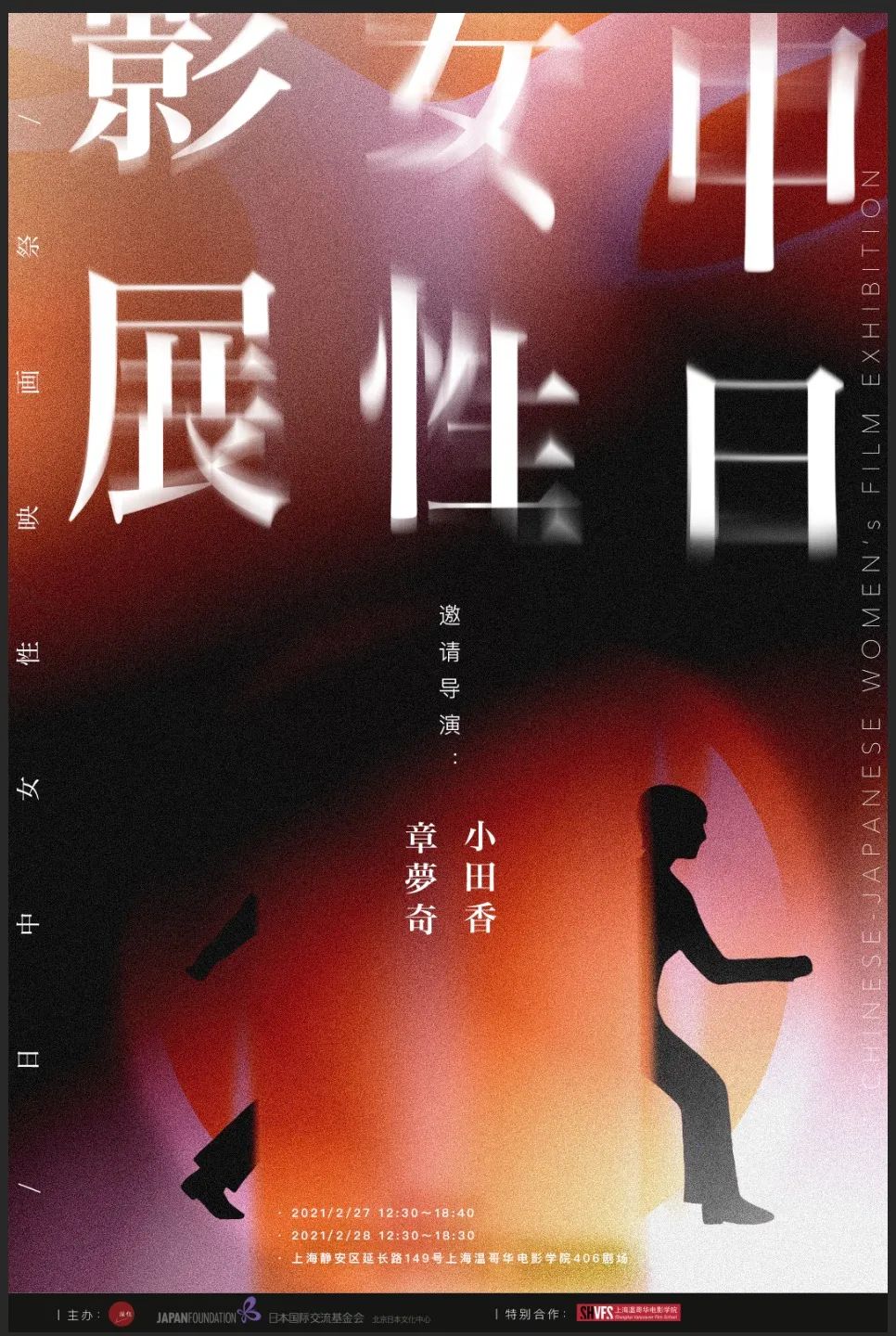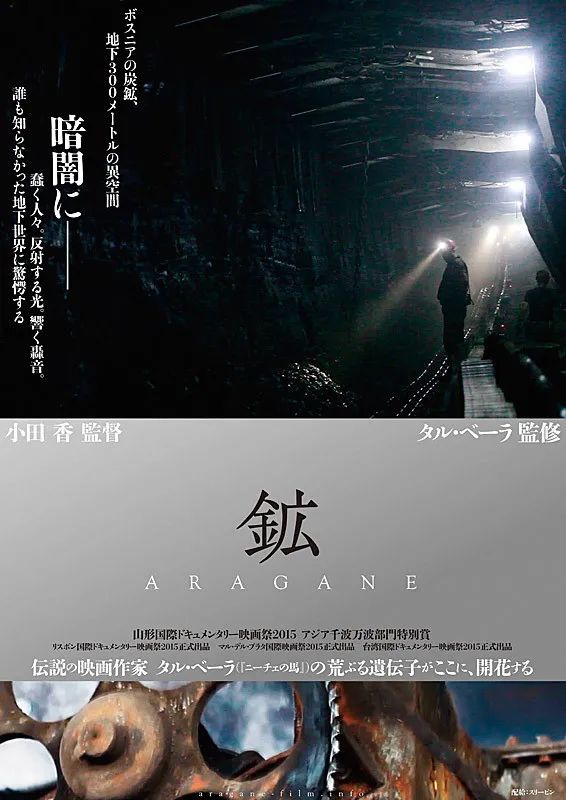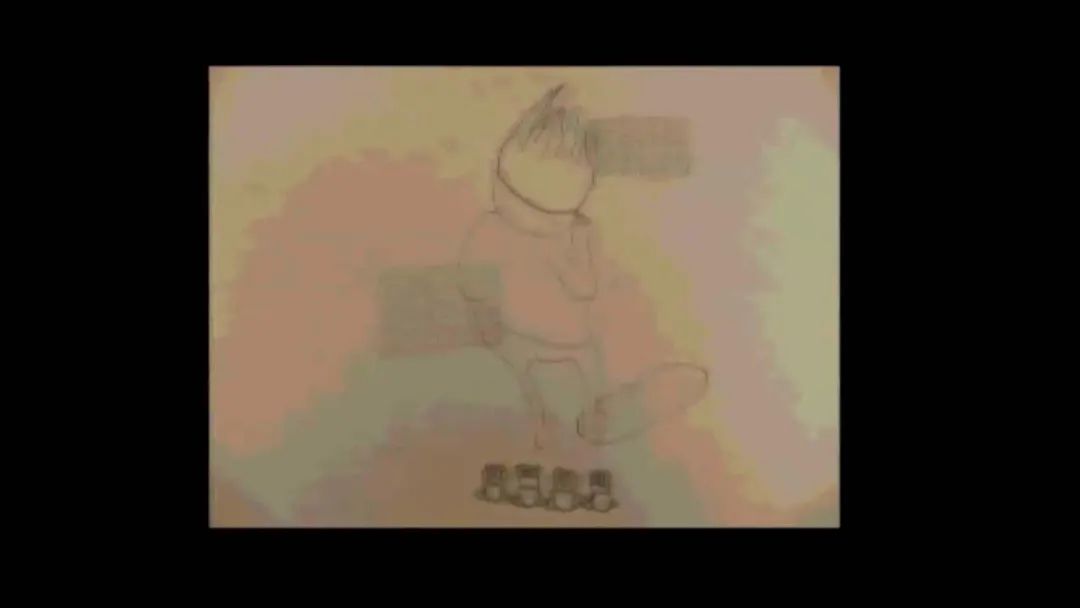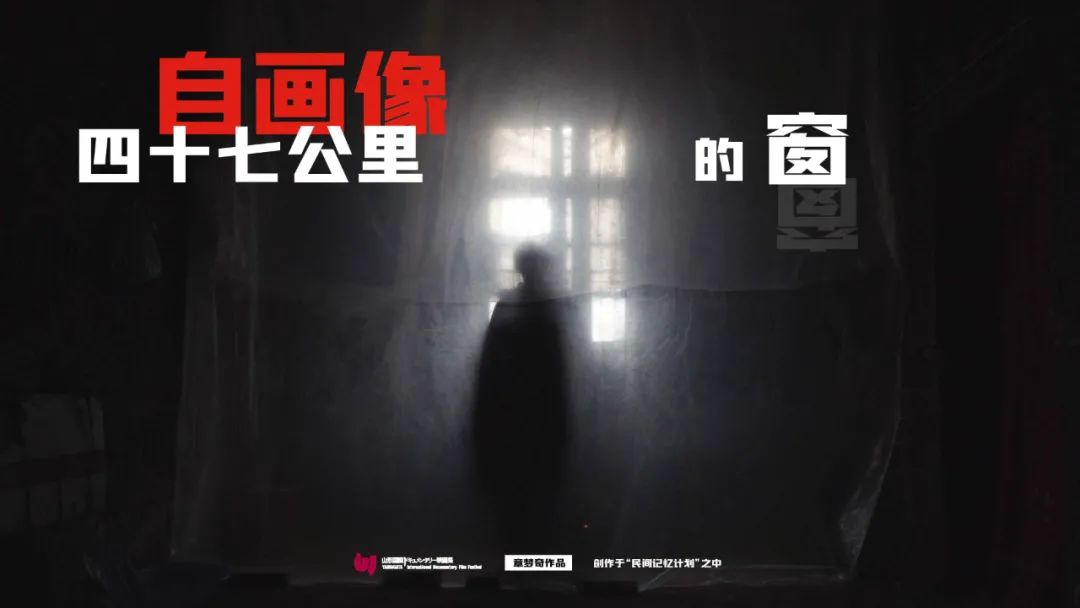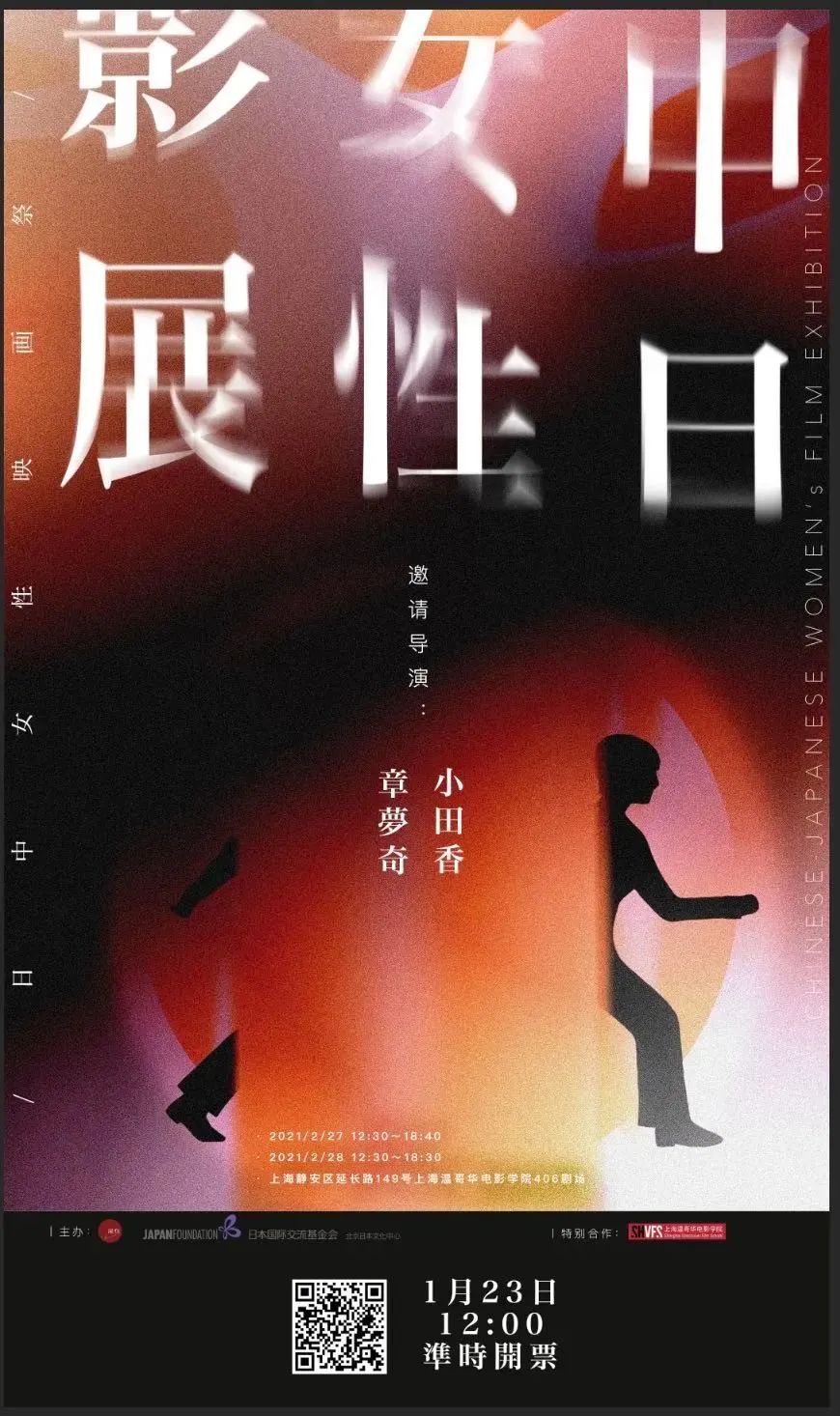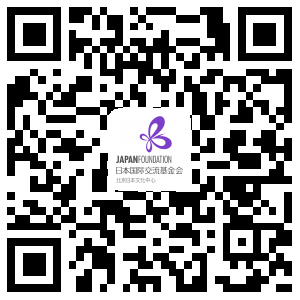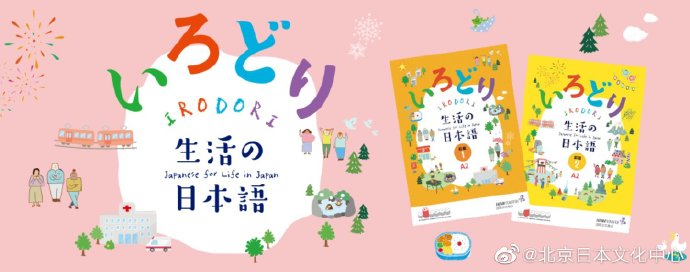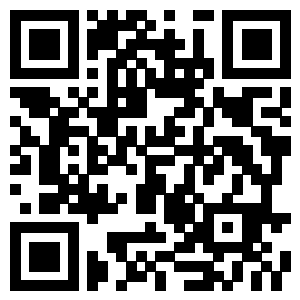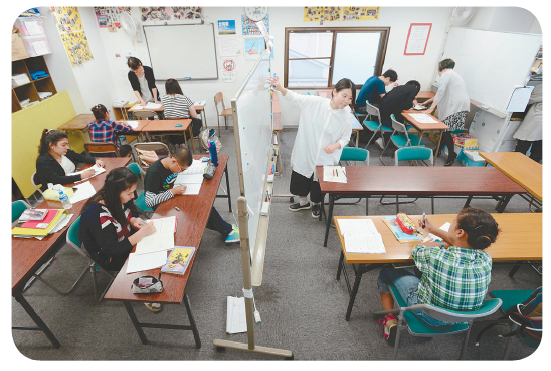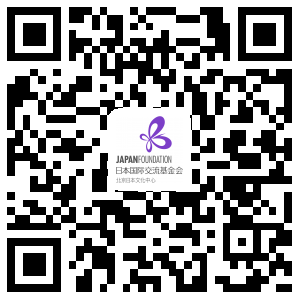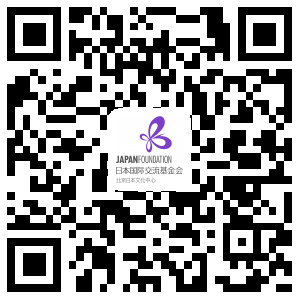特辑「新冠疫情影响之下的越境、交流、创造」系列访谈的第4期,邀请到了电影导演行定勋先生。在今年,行定勋导演的新作《剧场》于迷你影院和线上进行了同步公映;他还利用在线会议系统Zoom,制作了名为《A day in the home Series》的3部系列短片作品,同时开放免费的线上观看,由此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话题。此外,他也担任了家乡的熊本县「熊本复兴电影节2020」*¹ 的艺术总监一职,受他邀请的各位嘉宾皆如期到场,使电影节最终得以顺利举办。他通过上述种种行为,迫切地想把电影艺术持续传递给大众。
――正当因新冠疫情而相继取消电影上映之际,您已从2020年4月起就重启工作,制作了『A day in the home Series』系列,还在YouTube上进行免费公映,行动力真是非常之高啊。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的当今社会,比起“文化到底有多重要”这一问题,“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危机感则更胜一筹。我感到了文化果然是被大众相对的后置了,尤其是我们的电影和戏剧这类娱乐产业,皆被认为“如今不是讨论它们的时候”。
实际上,虽然此刻难以向外界传达出去,但确实仍有些人正以此为生计的继续工作着;而那些呼吁着不要熄灭文化之灯、发出寻求支援声音的人们也依然存在,所以我相信,至少有着一些人能够被作品所拯救,他们也仍依赖着文化的力量。
前路依然不甚明朗,即使解除紧急事态宣言,观众们还能否会选择走进电影院和剧院?身处这样停滞的状态,我如果不去行动,便无法传达心声。作为一个制作电影的人,我也只能选择去进行电影的创作。在我的演员当中,不乏有人对于接下来将要施展演技的地点和方式感到了不安,我再三劝说对方:“大家都是抱着同样的心情在家里参演,请再考虑一下吧。”从而最终完成了远程制作的3部线上作品。
我也通常会不自觉的陷入两难。如果是音乐,用一把吉他便可以贴近每个人的情绪;但电影却会变得非常麻烦。光是完成摄影、将其编辑并导入音效这一阶段,就会不知不觉的用掉了半年甚至一年时间。甚至在震灾刚过的时候,我们只是作为志愿者去放映电影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轻易就变成反倒给对方添乱的大型活动。
也许平时净是在思考这些事情,才让做线上放映的点子在今年从我的脑袋里冒了出来。
一切皆源于一次偶然,我在SNS上看到了有人借由Zoom(线上会议软件)组织了一个线上酒局,当时内心便浮现出了这样的想法:它的确是当下的一种文化现象,也记录下了疫情期间的生活日常,但我又能否来利用它讲述一个故事呢?人们可以通过它尽情交谈,虽然同时起头和回应会造成两头听不清的“事故”,但也都证明这段影像里的他们是真实处在同一时空。我认为即便是有剧本,也有可能产生真实感和生命力。
而经过这次尝试,我也受益良多。说实话,线上放映在此前对于我还是非常遥远的事物,我察觉到它最大的特点,即是可以把刚做好的东西马上给别人看到。像这样将刚发生的事情拍摄下来、制作成剧集并立刻上线公开的极速感,在我至今为止制作商业电影的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同时,这些由新冠疫情而产生的事件也能够因此被留下记录。留存时代的记忆是电影事业的使命之一,我认为线上作品也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您2004年的导演作品《今天发生的事件a day on the planet》*²是被2001年美国恐怖袭击事件(9.11)所触发而创作出来的;而在2016年,您也参与了为熊本地震的灾后重建而运作起来的“熊本复兴电影节”等活动,那么对于您来说,您为何会选择对当下的这些社会状况做出回应?
作为电影工作者,我觉得自己想要的不是试图去重构或破坏这个社会,而是寻找到人们那些能持续10年、20年不变的情感。
电影《今天发生的事件a day on the planet》也是如此,创作的契机虽然是9.11事件,在大环境中发生了如此巨大事件前提之下,故事里的他们依然照往常一般相约喝酒;而看起来无关紧要的酒局,实际也暗涌着许多复杂的情感。我想去刻画的正是那些隐藏在被认为是无聊的、琐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宝藏”。

以电影《今天发生的事件a day on the planet》命名的远程线上制作第一回《今天发生的事件a day in the home》场景之一(由导演本人提供)
我内心希望能够从一些细枝末节入手,以展现身处新冠疫情这样巨大漩涡当中的人们。虽然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事情和疫情并没有直接联系,甚至被点燃也仅由于过去的恋情——但他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让我感到人类果然还是拥有着强大力量的。仅此一点,就让我胸中燃起了希望。
我原以为除非是爆发世界大战,像现在这样全世界都停滞不动的状态是不会再有了……虽然很想相信世界大战已不会再发生,但我的内心还有着这样的想法:就算哀叹它是上帝同时给予我们的试炼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可情况或许并没有真正坏到我们所想的那个地步。
得知自己的电影无法按期上映,按理说我应当郁闷至极,但短篇作品的制作却让我重振旗鼓、变得积极。所以我意识到了一点:能将我从新冠疫情的情绪中拯救出来的,也还是我所热爱的电影事业。
——自政府发布新冠疫情的紧急事态宣言已经过去了半年,在此期间,您是否有所收获呢?
有的。从结果上来看,相信并期待这部电影的人果然还是存在的。在紧急事态宣言发布之后制作出来的《A day in the home Series》系列2部作品的观看人数(免费线上观看的人数总和),在一个月内已经超过了62万人,这个状况非常的令人欢欣鼓舞。
我认为在线播放会让一些计划外的观众有机会看到我的作品。虽然从做法上来说确也是利弊皆有,但只有如此,才最有可能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
话虽如此,我由衷希望大家还是去电影院看电影。
电影院的专业音响和巨幕画面可以给观众们施加魔法,让他们高度集中注意力;可线上放映就没办法施展这样的魔法——观看者不仅无法集中精力,甚至可以跳进或是停止观看。这样一来,就无法传达给他们电影原本的东西了。如果观众在电影一开始不被吸引,就会放弃观影,这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们所直面的困难也就越发的严峻:电影的节奏会被不自觉的越加越快,内容的选题也会逐步倾向那些让观众感到不无聊的东西。
对于日本电影,其情绪和留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相对更偏好一些老电影。当我们全身心投入到影院的黑暗中去,虽然可能会有无聊的时候,但其中也给我们留有进行思考的空隙,这就是所谓的“留白”。它果然是奢侈的时间与空间啊。
——摄影现场要依照防疫方针执行,也就是说密切接触的场景已无法拍摄了吧?最近几年数量激增的国际共同制作项目好像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也不是说就不能拍了吧。当然可以选择合成,或者让大家去做核酸检测,确认好了安全以后再拍,虽然这样就要花钱,且原定的日程计划也未必能赶上。所以现实里多数的情况还是延期到明年(2021年)以后。日本有些低成本少人数的摄制组还在持续工作,但如果是大制作,就要判断是否有必要花费大量时间和成倍的预算去维持拍摄进度。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也仍有人在坚持拍摄呢。
再说说国际合作项目。今年本来在台湾和韩国有拍摄计划,也准备邀请法国的女演员来日本进行拍摄,但因为目前无法自由的出入境,所以计划全都暂时搁置了。在现阶段,我也只能重新从零计划。
最近经常被询问到的要么是有关于新冠疫情本身、要么是新冠疫情之前、亦或是还未曾发生新冠疫情的世界…总之现在一切的原点就是新冠疫情。然而,绝大部分作品描绘的都是没有新冠疫情的世界,于是我开始思考:观看这些现代戏的观众还能否在其中感受到真实呢?
——在新冠疫情尘埃落定以后,Zoom和在线上放映也会成为你的工作标准之一吗?
不会,我觉得那不是一回事。目前在线播放的作品都是结合新冠疫情的有感而发所创作出来的,假若没有新冠疫情,这些作品就无法诞生。
但想想看,用譬如无法跨县移动这样的方式分隔地域,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强行拉开,再以此创作爱情故事,其实反倒是个非常巧妙的设定,让我不禁展开了联想。
异地恋的情侣们虽然可以使用在线通讯的手段去尽量缩短距离,但也确实无法做到再进一步的贴近彼此。
《感觉现在可以说出口》这部线上作品中,中井贵一与二阶堂富美探讨“我们真的合适吗”这一问题时,剧作家笔下的台词令我的心颤。人的心啊,虽然已试图去迎合对方,却由于无法缩短的距离让他们开始怀疑彼此是否真的合适。
不过能诞生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他们尝试靠近却无法与对方进行对视这点,让我觉得非常真实。
同样,创作出这些作品也是这个2020年度的收获,用Zoom进行艺术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很有意思…但,是否又真的可以一直用它进行电影的创作呢?Zoom作为当下文化趋势的一支,我想最起码在2020年内,它还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由中井贵一和二阶堂富美扮演情侣的第二期线上作品『感觉现在可以说出口』
(照片由导演本人提供)
——那在新冠疫情尘埃落定之后,您认为看电影的方式、及人与人的关系会产生变化吗?
是的,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人一旦失去了什么就会感到可惜,电影也是如此,在开始转向线上播放以后,我相信人们绝对是会想念电影院的。
但如果做电影的人不去相信“电影院绝对不会消失”这种话,那电影院可就真的会消失了。因为现实是会顺着人们心中所想而发展的。所以我强烈地认为电影院绝对不会消失,电影的表现方式也绝对不会改变。
另外,并不是因为《剧场》进行了线上线下同时发布,以后就都按着在线上映的方向发展,还是需要根据时机和场合来进行区分。觉得情况很快就会恢复所以选择暂时待机等待,这样的处理方式已经无法应对现在的情况。这也是今年电影业界受到巨大冲击的原因,我不希望让我身边的人也陷入那样的困境中去。
站在观众的角度,他们会有一种“总之我现在就是想看”的情绪,如果他们在上映推迟的期间看到同一个演员还有新作诞生的消息,这种情绪肯定也会发生变化。我认为观众们都是严格的,因此抱着“要想现在做的事情能够尽早传达给他们(观众),那么现在就必须拿出一些成果”的态度,决定线上线下同时发布。但由于这个决定偏离了映连(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映画制作者联盟)所制定的 “最初只在电影院进行公开的作品才能被承认是电影” 这一规则,我也历经迷惘,反复思量,最终还是考虑到能看到该作品的观众们,这才下定了决心。

2020年7月,于『剧场』首映当日的东京EUROSPACE(电影院名)前
我当时正想着,“现在的心情一生都不会忘记”(图片来自本人)
我们须认真对比线上放映与电影院放映的差别,并意识到这次的尝试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经此对比,就能够彻彻底底地将电影院的优点传达给大众了。
能否跨越地域的问题也是如此。通过线上当然可以看到对方,但那种想要和人面对面的心情一定会更为强烈:见到对方和倾听其所述,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实地体验,与线上交流的温度是绝对不同的。
就算你尝试通过网络与对方对峙,但眼睛究竟该看向哪里?你会发现很难与对方的视线对上是吧。我想这就是与人见面并传递情感的真正意义之一,且毋庸置疑。人和人的交往重要的正是关系的交错与连结。
——有了这种不自由的体验才能更加明白见面的重要啊。基于此认识,我想下一次的见面也会变得和之前不同吧。
是啊,会完全不同的。我们须再度认识到这样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和人的交往、一起推动事物发展又是多么重要。
如果思维定式可以进行变更的话,我想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呢:大家再借次机会同时停止,一起试着去思考同样的事情。如此一来能让社会变得更好也说不定。因为我觉得最后大概率会变成人人自省,毕竟在各自被隔离的状态之下,人们是会不自觉的将目光聚焦于自身的。
站在防疫的角度上,我也有些个人的想法。虽然电影院已被证实是个相对安全的场所,但在我的身边确实存在因家中确诊病患而无法返乡的人,况且我们也无从预判会有哪些人来到电影院。既然无法限制他人的行为,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想办法保护自己。
关于“传达”一事,我在《剧场》的上映期间悟出了一个道理,即“不给出清晰的选项就无法传递给想传递的人”。换言之,我们必须将自身立场透彻分析之后再进行选择,这才是重点。我认为政治上也应同理。
——如此想法上所产生的差异也遭到抨击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被断章取义了。我不清楚抨击别人对他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况且也不知道这些话又被套用在了哪里,语义可能也被扭曲得暧昧了起来。
正邪难辨的事情在社会上处处皆有,这才需要站在对方角度去进行思考。若是不好好去理解为何对方要如此处事,那不被理解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
如果因为感到麻烦只看了眼标题就觉得自己懂了,社会这样长此以往的发展下去也太可怕了吧。对于新冠病毒也是,有觉得它很可怕的人在,也有人觉得它并不可怕,这才是在这场复杂的灾难中最需要注意部分。
最终「熊本复兴电影节」决定于10月2日~4日期间召开。熊本县在「令和2年7月暴雨」的灾害中受灾情况严重,所以我们才产生了借助电影的力量为熊本县带来些许活力这一想法。
如果是在线上进行,那么我认为这个电影节原本的意义就会被排到新冠疫情之后,故而决定还是朝着邀请嘉宾、按原计划召开的方向继续推进。
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也不存在完美,因此在2020年,我的主题变成如何依照自己心中所想去行动,更况且实际做了以后可能也会获得启示呢。
大家为电影节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让场面的氛围有些许紧张;即使如此,电影中的角色们成功构建了极度亲密无间的人物关系,果然让那些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不可忘却的东西得以出现。正因身处疫情之中,定会有那些借机思考为人处世的观众前来观影,我认为创造这样的机会也是这次电影节召开所背负的责任之一。

熊本复兴电影节大幕拉上时的盛况(开幕式的现场,照片由导演本人提供)
——我们通过电影去和故事产生共鸣、想象登场人物的种种心情等等,也是身处当下社会所应具备的学习态度呢。
在此关键时刻,主人公的行动才会有更多能触动观众自身情绪的东西,特别是在感情方面。我察觉到现在的自己也陷入了这种状态。
毫无疑问,现在正是从纵向社会转变为横向社会的过渡期之中。在疫情期间,对于叫嚷着“赶紧救我们啊!”“像这样再继续为我们做下去啊!”的人们,有人觉得他们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自私自利,但事实却非如此——为这个国家缴纳税金的、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说这样的话。但这些叫嚷着的人也应当自发地联合起来,重要的难道不是大家手牵手肩并肩的团结一致吗?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甚至觉得,假如大家能够善于以合适的形式相互借用他人的发现就好了,长此以往,也许就能逐渐诞生出一个类似标准的东西。若只是在角落里净说些挑刺儿的话,那可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啦。
古人有云:“失败乃成功之母”。更何况,做实验什么的不就是要经历反复的失败吗?所以这些人才能创造出来新的东西,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那么对于在新冠疫情之下的社会,您又有何感想呢?
《A day in the home Series》是一部不可思议的作品。作为一部线上作品,它却寄托着“果然还是想去电影院啊”的强烈愿望。虽然以后可能也无法在电影院内看到它,但如果不是新冠疫情,便不会诞生这样的作品,更不会有后续的想法。我认为此刻当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可以跟大家重述电影艺术的美好。
如果整个世界能充满类似这样积极的发言就好了。倘若“这是错的!”之类的驳斥不再被用作挖苦他人,而是出于像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样的初衷,我想大家都会再度开口大声地表达意见的。
同样这也是一个让社会变得更为正直的契机。当世界像这样被静止,甚至连大气污染都稍微好些了不是吗。我想人类已经知晓自己造成地球污染所做下的种种恶行,接下来须不断地去深刻该认识即可。
但不管是我还是电影院,都一个须攻克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将最后的落脚点回到盈利上。
经此疫情应该能让一些人更加认识到一些问题,而自己如何去落实到实处才正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如果每个人都是如此去想去做,我们的社会应当会变得更好,我想这也会成为当今时代的电影主题吧。
*¹「熊本复兴电影节」……以2016年4月的熊本地震之复兴为目的,从2017年开始每年举办。所得收益全部捐赠于受灾地区的重建工程。
https://www.fukkoueigasai.jp/
*²『今天的事件 a day on the planet』……某天夜里,一群伙伴为庆祝成功考入京都的大学研究所的朋友乔迁新居而相聚一起。但现场却暗涌着无法用语言传达的种种心情。本作品为芥川奖获奖者·柴崎友香出道作的电影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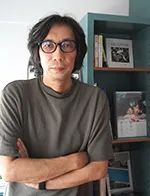
生于1968年,熊本县人。长篇第一部作品《向日葵的声音》(2000年)在第五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国际影评人协会奖,并作为具备导演能力的新锐创作者而备受期待。作品《GO!大暴走》(2001年)以第25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奖为开始崭露头角,并囊括诸多奖项;《在世界中心呼唤爱》(2004年)的票房收入达到85亿日元,甚至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之后,《北之零年》(2005年)、《春之雪》(2005年)、《尘封笔记本》(2007年)、《爱妻家》(2010年)、《检阅式》(2010年/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的费比西奖)、在上海拍摄的日中合作作品《深夜前的五分钟》(2014年)、《粉与灰》(2016年)、《Naratage》(2017年)等作品陆续发布,《Reverse Edge》(2018年)在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获得第2次费比西奖。2020年,又吉直树原作的电影《剧场》于7月17日起在日本全国20家小剧场上映,并在Amazon Prime Video上同时发布。同年还将水城雪可奈漫画原作进行电影化,由大仓忠义、成田凌出演的《穷途鼠的奶酪梦》于9月11日上映。另外,作为支持政府的自我限制外出企划,还发表了线上电影《今天的事件a day in the home》、《感觉现在可以说出口》、《去电影院的日子》(都于Hulu发布)等,精神充沛地进行着创作活动。
采访、撰文、摄影:寺江瞳(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北川富朗•艺术总监|专题【新型冠状病毒下的越境、交流、创造】Vol.3
专题【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越境、交流、创造】 预告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